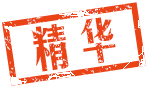本帖最后由 杨云辉 于 2025-6-30 08:00 编辑
锡矿山:百年矿区的惊世蝶变
杨云辉
山岚如轻纱漫卷,将晨雾揉成流动的云絮,丝丝缕缕缠绕在苍翠欲滴的峰峦间。我驻足于观景台的雕花栏杆旁,眼前铺展的是一幅浓墨重彩的生态长卷——层层叠叠的新绿似潮水般奔涌,蔷薇花攀着铁艺围栏舒展柔蔓,迎春花垂落的枝条将晨曦酿成翠绿色的蜜。谁能想象,这片被蜂蝶簇拥、被鸟鸣浸润的土地,曾是布满疮痍的采矿废墟?从烟尘蔽日的工业战场到繁花似锦的生态长廊,锡矿山用二十年光阴,在岩层褶皱里镌刻出一部震撼人心的重生史诗。
百年前的故事,始于一场跨越世纪的“美丽误会”。1897年深秋的某个清晨,探矿人举着煤油灯俯身在矿脉前,银灰色的矿石在昏黄光影里泛着锡器般的光泽,“锡矿山”的名字就此传开。从此,沉寂亿万年的地层被唤醒,一盏盏矿灯如同坠落人间的星辰,照亮了蜿蜒千米的巷道。抗战的烽火中,这里产出的锑矿石化作枪炮弹药,在华北平原上划出捍卫国土的弧线;新中国建设的浪潮里,满载矿石的火车汽笛长鸣,将“世界锑都”的荣耀带向祖国四方。矿工们结满老茧的手掌紧握钢钎,在岩层间凿刻出民族工业的脊梁,浸透汗水的粗布背带裤,在岁月里沉淀成永不褪色的勋章。
然而,过度开采的代价如阴霾悄然笼罩。昔日欢唱的溪流被矿渣染成铁锈色,如同大地无法愈合的伤口;苍翠的山坡褪去绿装,裸露出灰白岩体,恰似嶙峋的骨骼在风中呜咽。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粉尘,将蓝天撕成破碎的画布,连穿透云层的阳光都蒙上一层病态的灰白。当生态警报拉响,锡矿山人毅然放下沉重的镐头,以壮士断腕的决心,开启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态救赎。
转型的征程,是一曲与自然和解的深情长调。工程队如修复古籍的匠人,戴着防尘面罩清理尾矿库的废渣,每一块碎石都被编号归位;他们用钢筋铁骨加固松动的山体,如同为大地穿上坚固的铠甲。背着树苗的工人腰系安全绳,在近乎垂直的山坡上攀爬,将一袋袋客土填入矿坑,就像为土地敷上治愈的膏药。春雨浸润的时节,漫山遍野的树苗破土而出,幼嫩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生命的倔强。年复一年,死寂的尾矿库蓄满了清澈的雨水,摇身变成波光粼粼的人工湖,成群的水鸟掠过水面,惊起圈圈涟漪;裸露的岩壁上,爬山等藤类植物织就翡翠色的绒毯,野杜鹃在石缝间绽放,将荒芜点缀成绚烂的调色盘。
产业升级的浪潮中,锡矿山完成了从粗犷到精致的蜕变。传统矿企的巷道里,智能采矿设备闪烁着幽蓝的指示灯,智能选矿机精准抓取矿石的动作如同优雅的芭蕾;科研基地的实验室彻夜通明,显微镜下的锑元素结晶,在灯光下折射出星辰般的光芒。最惊艳的当属“工业 + 文旅”的神来之笔——废弃矿洞被改造成时光隧道,斑驳岩壁上,全息投影重现着百年前矿工举着马灯艰难前行的身影;生锈的选矿厂化身文创集市,老式矿车改造成流动花车,风镐、钻头被艺术家用焊枪重塑成巨型机械雕塑,齿轮与藤蔓共生,铁锈与繁花交织。
如今的锡矿山,每一帧画面都是精心雕琢的艺术。踏入“玫瑰爱琴海”景区,70亩玫瑰如燃烧的云霞铺展在地平线,红的似跳跃的火焰、粉的如少女的腮红、白的胜冬日的初雪,馥郁的芬芳引得蜜蜂载歌载舞。悬浮于花海之上的观景露台,以废旧矿梯为骨架,钢化玻璃为肌肤,游客凭栏远眺,可见“万马奔腾”石林在花海中昂首嘶鸣——上千根石柱状如骏马,纹理恰似被岁月雕刻的鬃毛,在微风中似要踏云而去。彩虹步道蜿蜒其间,路面嵌着不同年代的矿石标本,孩童们蹲在“锑矿石星图”旁,用放大镜探寻亿万年前的地质密码。
红色记忆在这里焕发新生。锡矿山展览馆内,声光电交织的展厅中,老矿工的蜡像栩栩如生,他们粗糙的手掌还紧握着当年的矿灯;展柜里的锑矿奇石形态万千,有的如水晶宫般剔透,内部包裹着远古的气泡,有的似火焰山般炽热,赤红纹路如大地的血脉,无声诉说着大地的鬼斧神工。羊牯岭碉楼的砖石间,仿佛还回荡着革命志士的铿锵誓言;红军亭内,老党员布满皱纹的手轻抚斑驳立柱,向孩子们讲述红二六军团在此扩红筹粮的热血往事,阳光透过木质格栅,在地面投下金色的菱形光斑。段家大院的雕花窗棂后,陈列着泛黄的采矿契约,墨迹里藏着矿业先驱的传奇人生,留声机里传来的老唱片旋律,与院外的虫鸣鸟叫交织成时空交响。
暮色四合时,归鸟掠过新植的松树林,将夕阳剪成金色的碎片。曾经轰鸣的矿区,如今飘来文创集市的民谣弹唱,矿工食堂变身网红打卡地,铁饭盒里盛着改良后的矿嫂私房菜,腊肉的醇香混着野山菌的清甜。霓虹初上,“忆苦窿”遗址前,游客戴着设备“穿越”回旧社会,在虚拟巷道中感受矿工们挥汗如雨的艰辛。山风拂过修复后的梯田,稻浪与不远处的工业遗址交相辉映,诉说着这座矿山浴火重生的奇迹。
锡矿山的华丽转身,是一封写给大地的情书。它用伤痕累累的过往,换来与自然和解的未来;用厚重的工业遗产,编织出文旅融合的锦绣。当月光为这片涅槃重生的土地披上银纱,我终于读懂:真正的繁荣,不是对资源的无尽索取,而是在守护与创新中,让每一寸土地都绽放出生命的光彩。
|